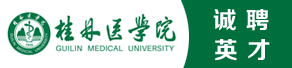本报驻美国、英国、德国特约记者 田秋 纪双城 青木 本报记者 赵觉珵
新冠疫情在全球仍在蔓延,一些符合撤侨条件的未成年中国留学生近段时间陆续回国。但对于大量的“大龄留学生”——拖家带口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生,回国似乎不再是个可行的方案。同时,许多人平时身兼助教、助研身份,因疫情学校停课之后,他们一部分重要的生活收入也被大大削减。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学生如何平衡学习、学校工作与家庭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
回国难,维持科研更难
听到疫情中一些留学生回国的消息时,许多在美国的博士生一时间燃起了希望。然而经过了解他们才发现,我国为新冠疫情中滞留海外的留学生提供的回国包机主要针对生活有困难的未成年人,而博士生的年龄绝大部分在30岁上下。除了跨国家庭产生的困扰外,他们的科研进度也大打折扣。
对于一些大龄留学生来说,他们的家庭成员在当地也拥有暂时就读的学校或就职的单位,令他们的灵活性大大降低。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张女士的孩子正在当地上小学,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两个人的机票过于昂贵,我也担心孩子能否承受长时间飞行的风险”,她在无奈中取消了暑假回国的计划。同样正在攻读博士的黄女士的丈夫目前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公司不允许员工出境,为了家庭成员不分散,只好继续留在美国”。
相比于高中甚至本科等可以得到一些国内家庭支持的留学生,博士生大多经济独立,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助教助研职位和校内打工。然而近段时间,陆续有美国学校宣布2020-2021学年的第一学期甚至前半年,都可能采用远程上课的方式,很多博士生失去夏季找到临时工作和实习的机会,对未来一年的经费问题有了忧虑。远程教学对担任助教的不少学生带来一些“不公平”。对于美国高校来说,全部课程转为线上的决定十分突然,随之而来的额外工作——把课堂材料传到网上、熟练使用网课软件等繁琐的任务,往往都落在助教身上,而他们对这一部分额外的投入并不会获得酬劳,有些学生认为这是对已经高强度、低工资的博士生的一种“剥削”。
无法使用校内资源和设施成为“科研至上”的博士生的一大困惑。博士生阅读和写作量要远远大于本科生和硕士生,因为图书馆关闭,许多学生为了完成日常的学习和科研任务,不得不自行购买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图书馆取得的资料。《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学生如果买一本较新发行的科研类书籍,平均价格都要在100美元左右,有些甚至高达600-700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除此之外,免费或低价扫描、打印等校园设施也停止开放,许多学生还需额外购买打印机、扫描仪等。
即便家人可以随自己同行回国,很多留学生也要经历一番“麻烦”。陈先生是在英国纽卡斯尔当地就读研究生的一名“大龄留学生”。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最大的麻烦是毕业论文。陈先生学习的是城市规划,毕业论文原本计划是比较中国与英国二线城市近些年的城市规划。英国从3月宣布封城之后,陈先生考虑到妻子和孩子的健康问题,一家人一起订了机票回国。但对于他个人来说,上学和毕业后回国找工作就形成了一个“时差”问题:原本他在英国的研究生课程计划为一年,即便现在独自返回英国,完成论文的英国调研部分,也仍然会受到当地禁足令的影响。论文的进度会影响毕业进度,进而影响未来再就职的情况。今年已经37岁的陈先生现在正为是否要申请延迟毕业,左右为难。
31岁的李静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本来希望和家人一起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德国。疫情期间,她无法进入实验室,严重影响科研进度。现在,大学已开学,她也开始去学校做些工作,但学生仍未开始正式上课。
各种生活费用暴涨
虽然一些海外高校已经调整了宿舍的人员密度,但是继续居住在宿舍里依然存在较高风险。在美国读博士的王女士住在学校的“家庭宿舍”,即一家人可以单住一间公寓,不需要与其他学生同住一户,但洗衣房等设施依然是整个小区共用的。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很担心大家共用洗衣房和洗衣机会传播病菌,但是也别无选择。”另外,因为博士生在校时间长,通常为5-7年,他们的生活物品更多,在疫情中一些人面临被房东强制退租的危机,更是要遭受不少经济损失和精神压力。
疫情之下多国实行的居家令也让学生的生活费用暴涨,甚至难以保障基本生活。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美中国博士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我们只能网购食材和生活用品,不仅价格比平时贵了很多,运费也非常昂贵。我们偶尔也会叫外卖,但是费用比学校食堂贵太多了,还需要支付服务费、送餐费和小费等。”另外,疫情也让大家难以保持原本“中国式”生活习惯——“现在只能就近去周边的美国超市和便利店,没法再特意去较远的中国超市了,大米、葱姜蒜、酱油都成了稀缺商品,想要自己做饭,真是难上加难”。
在德国的大学中,读硕士和博士的留学生比例较高,年龄层整体较大,他们对待疫情也更为冷静。25岁的韩志在德国西部的波鸿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不多。“现在买不到机票,也不符合未成年撤侨条件,回国途中乘机也是一个不安全因素。”在德国,他们只能保证我不出门,不社交,“只在进行必要的购物时全副武装出门”。韩志也表示,疫情对留学生的影响很大,可能导致许多人无法毕业。经济上也出现问题。他本来在一家公司兼职,每月可获得约500欧元的收入,疫情中他失业了。
李静的孩子在当地大学的附属幼儿园上学,但目前还在闭园中,只能由在家远程办公的丈夫照顾。她告诉记者:“在德国读博士相当于工作,要签合同,每月除了医疗保险等外,可以获得约1000欧元工资。疫情期间,如果博士生不工作,还可以获得‘短时工作’补贴,相当于平时月工资的60%-80%。”李静认为,学校和社会会帮助解决很多问题,“关键是留学生不要脱离大学”。现在,德国政府向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学生提供每月最多650欧元的免息贷款,有特别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向学生管理委员会申请紧急补贴,最多一次性获得500欧元。李静表示,一定要与导师、同学、学生管理委员会等保持联系,了解各种信息。如果在经济有问题,也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助。
职业规划受到巨大影响
特殊时期中的留学生活,大大影响了硕博士生对未来的规划。一是因补助不到位导致资金来源问题,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些高材生开始考虑与原有计划不同的出路。
在伦敦当地某大学修读工商管理的张女士告诉记者,最近两个月她和不少中国同学都在向学校申请讨还停课造成的学费损失。她说,学费约3万英镑,大家认为至少应退回一半,但校方至今没有松口。今年34岁的张女士说,语言障碍导致她无法“单枪匹马”与校方周旋,伴随暑假一天天逼近,留学时间也在缩短,最后可能会不了了之。
对于一些大龄留学生来说,临时工或是实习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当地找到就业机会的跳板,但眼下多数英国企业都还没有复工,更多人开始考虑毕业后回国找工作。
澳大利亚近期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一直遭到质疑。一些澳大利亚高校宣布对国际学生发放资金补贴,然而过去的一个月中,多个外媒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对受困留学生的支持力度不足,一些高校承诺的补助也没有到位。《悉尼先驱晨报》曾以“澳大利亚在国际学生方面答零分”为题称,这些学生因为身份问题无法获得政府福利,更无法拿到失业补助。英国《卫报》也称,大量留学生这段时间在澳大利亚甚至只能通过社区扶贫的免费食物来解决一日三餐。
与此同时,一批已经收到澳高校录取通知书、辞职准备赴澳就读的中国大龄留学生,更是夹在澳政府迟迟不给签证与高校有名无实的补助的困境中。今年年初,《环球时报》记者曾收到上百名准备赴澳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联名信,讲述了他们“苦等澳大利亚签证无果”的共同经历。几个月过去,“卡签证”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个由被澳大利亚“卡签证”的中国学生组成的QQ群中,《环球时报》记者看到了380名成员。杨同学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表格,其中记录了187名目前在等待签证的中国学生的信息,其中等待最久的时间长达21个月,2/3的人都已经等待半年以上,有20人等待时间超过一年。多名接受采访的学生表示,他们大多是科学类或工程类专业的硕博士生,这或许被澳大利亚视为敏感专业。
由于不知何时能够得到签证,很多中国学生的学业和工作计划完全被打乱。杨同学在2019年7月拿到墨尔本大学化学博士录取通知书,随后便辞去工作,“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在漫长且不知期限的等待中,已经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选择换学校、找工作。一名申请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同学表示,虽然他在5月刚刚获得签证,但由于疫情影响,前往澳洲也遥遥无期,因此选择放弃。他告诉记者,签证的拖延,可能对回国后参加各种青年学者计划影响很大。
美国高校纷纷宣布新学年暂缓聘用新的教职工,对于原本要在今年夏天毕业并开始找工作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七八年的辛苦,却要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真的很令人绝望。而在当下的情况下,虽然学校允许延期毕业,但是奖学金已经用完,经费又从哪里来呢?”不止一名中国博士生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了这一焦虑。除了学术界的工作职位空前紧张以外,业界的工作机会也大大减少了,“目前很多公司都宣布暂缓招人,原定夏季和秋季入职的职位都很难保证。”
同样担心留学生无法留下来工作的,还有当地的企业。美国《福布斯》等多家媒体称,在疫情与签证收紧的双重夹击下,更多中国留学生可能会选择回国或去如加拿大等签证政策更宽松的国家。美国《国家法律评论》杂志称,有当地企业认为,一些关键职位“只有国际毕业生能担当”,失去这部分潜在的高级职工,这些企业可能会失去和外企的竞争力。